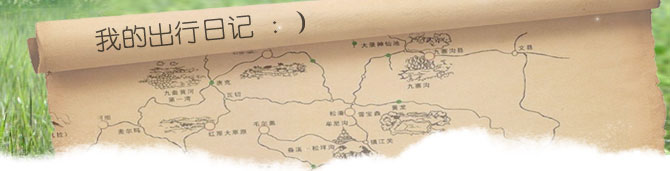这一天的日程决不可以用悠闲来界定。为了赶上唯一的的班船,我们必须在中午前赶到培石,与前一天就出发的片片和施子会合。接近八点的时候,在第一缕晨曦的辉映下,我们告别了神女,继续我们在巫峡的旅程。
行走于天地间,留下坚实的足迹,书写属于自己的历史。不经意间,个人的历史融入广阔的时代背景,我们一不小心成了一段史实的见证人。
记得以前见过一张无夺桥的照片:清澈秀美的甲板溪上,古老、沧桑的一座单孔石桥,黄沙湮没了桥面,绿草如茵倾覆其上,显示出勃勃生机,仿佛在暗示人们:“纵然我老,身子骨还硬朗,有力气站在这里承载南来北往的行路人。”可是,六月,长江水就要一寸寸涨上来。过去也有江水淹没桥面的事情,但水很快就退下去了。这次不同,这里将永沉水底。所以,无夺桥将迫不得已被拆掉。
很难想象如果我们迟到半个小时,或者如果拆桥民工早起半个小时会发生怎样的变化。其实也很简单,大的历史不会更改:无夺桥因三峡工程建设的需要被拆除。我们个人的历史却会被改写:错过了从无夺桥上走过的机会。好在这样的如果并未成为现实。我们及时赶到,拆桥民工还在吃早饭。工人们说,吃过早饭他们就要动手拆除余下的部分。建造这座桥或许要花上好几个月的工夫,把它拆掉却只用得着几个小时。经过向管事的多次请求,他终于同意通融一下,让我们过桥。无夺桥的桥面已经拆了,周身被脚手架和竹制跳板包裹,道路和剩余桥体之间形成的陡坡也给我们制造了不小的难度。当最后一个人通过时,我看到民工们已经放下了饭碗,拿上了工具。我们成了最后通过无夺桥的行人!
无夺桥,名字听起来怪怪的,让人记忆深刻。遍查各种资料都没有关于此名来历的记载。我冒昧臆测,过去人们过甲板溪只能涉水或乘摆渡,洪水来临时很容易出人命;后来建起了无夺桥,以其“桥既成,无使再夺人性命”之意命名。自清朝建成以来,无夺桥送别的人怕是已成千上万了吧。而今,面对它的离去,送别的只有我们十几个人。
作者:cqct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