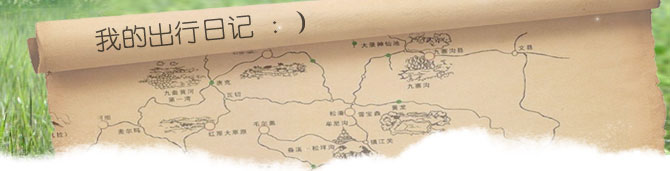德格印经院
说起来我们的运气实在不错。去德格搭的车,司机一家自己也要到印经院转转。并且陪着司机的小舅子是德格地方上的头脸人物。而我们,自然不请自来,堂而皇之地兼做司机随从,不仅有导游,还可以随便拍照。
一进入印经院,就觉得,我来到了一个与世隔离的地方。
建筑外体颜色很新,仿佛是刷过不久。连接大门是一条长廊,尽头是一个长而窄的天井,四面围着高墙。站在天井里抬眼,红色的墙壁延伸的尽头,是一块蔚蓝色而纯净的天。时间仿佛就凝固在这里,300年的风风雨雨,就凝固在这一小块长而狭的天地之间。
门口一间小房间里,两位老人在调配红色的墨浆,用来涂红色的雕版。墨浆放在一个大木桶里,老人各坐一边,一个用木棍不断地搅拌,另一个则适时地加入新的原料。他们就这样,一种单一的节奏,一天又一天,一年又一年,从开始的那一天开始,却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结束。
大殿关闭着。沿着天井爬上楼梯,迎面就是一整排的柜子。走在一个一个高高的柜子之间,窗口射进来的光就像被吸引掉,保持着房间的阴暗与沉重。印板就一排一排地放在这些柜子上,柜子的每一格都有标签标注。“丹珠尔”,“甘珠尔”……
中间是工人们工作的地方了。每年这里都会聘请将近100名临时工,担任印刷的工作。
这个殿大约有20组人,每组2人,放纸,给纸上墨,揭纸,给雕版上墨;放纸,给纸上墨,揭纸,给雕版上墨;放纸,给纸上墨,揭纸,给雕版上墨;……2秒钟一个循环,2秒钟一张经文。
站在一旁看着他们工作,我忽然觉得那似乎是20部机器在运作。那样的速度,那样的流程,与机器没有什么两样。可是,那样的工作,我不知道那些工人是带着怎样的感情去做这样机械的事情,或者根本就没有感情。我一直看着他们,他们却始终没有抬过眼看我。或许他们已经习惯了,习惯了这样的工作,习惯了这样的注视,习惯了这样的生活。
我不知道300年前,是不是就这样操作;我不知道30年后,还会不会保留这样的操作。我只知道,现在,在这间昏暗的房间里,工匠们,聚在唯一有光照到的地方,机械地工作着,为了每天的食物和衣服。
我站在这里,忽然觉得有些荒谬。我带着一部有摄像功能的数码相机,带着一架有20G存贮量和MP3功能的移动硬盘。我看着几十个人在努力工作,用已经淘汰了几十年甚至百年的方法。我不知道,这些工匠是不是也包括在参观的范畴当中。然而,对于他们,这却不是历史的陈列,而是实实在在的生活。
“印经院在申请世界遗产。旁边的这些新盖的房子以后都要拆,只有那些旧房子可能会留下来。”
……
“如果成功,这里就好了。来的人会更多。什么宾馆饭店都可以建起来,门票也要收高一点。……”
作者:happylee